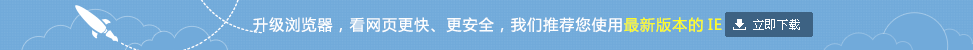面對國際油價長期低位徘徊的現實,部分財政高度依賴油氣出國的資源國采取了許多新政策。委內瑞拉將國內95號汽油價格提高了600倍,沙特準備歷史上第一次進入海外債券市場。那么,低油價對主要產油國政治、經濟形勢產生了哪些影響?相關國家采取了哪些應對措施?還有哪些政策儲備?

油氣生產國如何應對低油價困境
首先要看到的是,低油價主要沖擊到產油國財政,而非其大型能源企業。大型能源企業一般都具有比較完整的產業鏈,從勘探開發、運輸、煉化,直至終端的配送、加油站和附屬的零售服務等,不一而足。國際油氣價格的下降雖然導致大型能源企業上游產業利潤下滑,但其煉化和零售端仍可保持盈利,確保了企業整體依然保持一定的利潤率。俄油、俄氣、沙美等油氣巨頭不僅上游儲備豐富,亦有競爭力很強的下游產業,因而能夠在低油價時代保持總體的盈利。因此,產油國應對低油價的政策目標主要包括阻遏國際油價進一步下滑、緩解國家財政困難、開拓市場、確保困難時期政治安全穩定、調整產業結構等。
壓縮公共開支,緩解財政壓力是產油國的首要政策選項。伊朗、阿聯酋、伊拉克、沙特、俄羅斯等重要油氣生產國財政收入高度依賴油氣資源出口。其油價—— 財政均衡點普遍處于70美元/桶至100美元/桶區間,遠高于當前40美元/桶左右的國際油價。沙特、俄羅斯雖然在高油價時期積累了大量的外匯儲備,但單一的經濟結構和巨額財政赤字都不容其坐吃山空。由于大量的資本外逃,俄羅斯面臨的經濟財政形勢還要更嚴峻一些。面對困難,沙特、委內瑞拉、印尼等國近來紛紛大幅度壓縮化石能源補貼、控制公共部門支出。
如沙特去年年底將能源及用電補貼大幅度縮減了45%;尼日利亞、阿塞拜疆在大幅度壓縮政府開支的同時,也開始向世界銀行和國際債券市場尋求資金;面對西方制裁,俄羅斯難以獲得國際金融支持,但其通過盧布貶值,在一定程度上對沖了油價風險。所有這些政策選項或可在短時間內騰挪資金,但長期壓縮公共開支必然引起社會反彈,舉債度日則要負擔巨額利息并承受債務違約帶來的信用風險,均不是治本之策。持續的貨幣貶值更會對國家經濟社會運行與國際貿易帶來致命打擊。
調整產業結構是油氣生產國應對低油價困境的治本之策。海合會六國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就開始積極開拓非石油經濟的發展。阿聯酋政府積極投資非石油產業,產值已占其國民生產總值(GDP)的一半以上。沙特國家工業化發展戰略明確提出,至2020年工業產值占GDP比重要達到20%。阿曼在其漫長的海岸線上建立了一系列工業園區、自貿區,打造地區轉口貿易中心。俄羅斯同樣將產業結構調整作為國家戰略加以推行。但其面臨保增長與調結構、利用比較優勢還是后發優勢、經濟改革與政治穩定等多重兩難,產業結構的優化難以一蹴而就。
普京總統執政以來以能源立國,產業結構調整進展不佳,持續了多年的高油價更加深了俄羅斯經濟結構對油氣資源出口的依賴。實際上,資源陷阱是油氣富集國的經濟魔咒——可以依靠天賦資源過好日子,哪來的動力開展艱苦的工業化和經濟結構調整過程?所謂“卓越出自艱辛”“多難興邦”,大抵就是此意。
在聯合減產協議難以達成的背景下,凍結產能似乎成了唯一選擇。然而,西亞北非復雜的地緣政治與經濟矛盾又一次壓倒了油價下行造成的財政壓力——沙特堅決不同意簽署一項沒有伊朗參與的凍產協議;多哈回合談判無果而終。實際上,業界已經形成的產能早已固化,即便產能凍結協議達成,也并不意味著既成的供給富余行將消失。換而言之,即便今后達成產能凍結協議,也只能引起油價短期內的上揚。而從中長期來看,如果全球經濟無法實現有力復蘇,油氣需求不能實現強勁增長,國際油價遠期曲線仍將走低。
國際能源署預測,由于油氣產業投資大幅削減,2020年國際油價將上漲到80美元/桶——這將超過多數產油國財政的平衡點。擺脫“資源魔咒”,真正實現產業結構的多元化,需要產油國決策層拿出更強的政治決心。阿聯酋已經提出計劃,未來50年將油氣產業對GDP的貢獻降到零。
由于新能源和油氣開采技術的不斷進步,全球技術可獲得能源總量不斷增加。至2050年,全球每年可獲得能源總量將達到4550億噸油當量,是有效需求的20多倍,風、光、水、核等新能源占據了其中的絕大部分。盡管人類仍將長期處于化石能源時代,但新能源對油氣消費增量的擠壓已經成為現實。油氣生產國面臨的不僅是低油價的沖擊,更要面對技術進步帶來的充沛能源供給的挑戰。
低油價時代帶給產油國的不僅是經濟困難,同時也是倒逼產業結構調整的動力,從根本上擺脫資源陷阱,產油國應早做打算。